書籍出版 > 書籍資料
本書以「理」為名,曰《玄理與性理》,是一部言理之書,雖所涉以魏晉玄學之論題為主,所論卻是普遍的理的問題。以魏晉玄學論題來展開,只因魏晉人最善談理,玄學時代為中國思想史中最哲學,最富方法學意識,湧現最多哲學範疇之時代。本書藉重構魏晉玄學之兩大課題︰「言意之辨」(方法學)與「自然與名教」(時代中心論題),把道家玄理與儒家性理帶進現代哲學言說之域──令人覺得意味深長的是,「言意之辨(語言哲學)」、「自然(自由)與名教(道德倫理)」亦正是當代哲學的關注中心。
本書名「玄理與性理」,非謂天地間自有各種理,道家揀個「玄理」,儒家挑個「性理」,今論二理之得失及其關連也。本書認為,天地間自有理,然皆不離人心之活動與作用,心動理立,心明理察,心靜理直(或寂),故謂心即理;非僅此也,本書更認為,人同此心,唯心之動靜非一,故心一而理殊,然殊理同歸一心,殊途同歸一理,而理一分殊,分一命殊,此之謂性理;即心言性,即性言理。然心不僅可具眾理,且可統眾理、會眾理以至平鋪眾理、寂化眾理,無而能有,有而能無,攝存在於活動,即存在即不存在,玄之又玄,眾妙之門,此之謂玄理。此則是心之活動本身內在之「有、無、玄」之理。心只是一心,人卻萬殊,理則多途,如何可以言說之、授受之?是證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所謂「超越而內在」。是本書與《實證與唯心》相呼應,為實證唯心論之理學篇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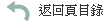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 回頁首
回頁首